【隐患】
上一篇提到了土豆的种种优势,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土豆为这些好处也付出了许多代价。
首先,这种随时储藏的策略毕竟没有最大发挥自己的潜力,因此当环境适宜水肥充足时,土豆依然不是水稻小麦的对手。所以目前的土豆种植量虽在发展中国家以每年5%速率增长,在发达国家却以每年1%速率下降;而在全球粮食体系中,土豆仍然只能屈居第四。不过,这当然并不妨碍爱尔兰的穷苦农民大量种植土豆,也不妨碍粮农组织总干事雅克·迪乌夫称赞说“马铃薯在战胜世界饥饿和贫困斗争的前沿发挥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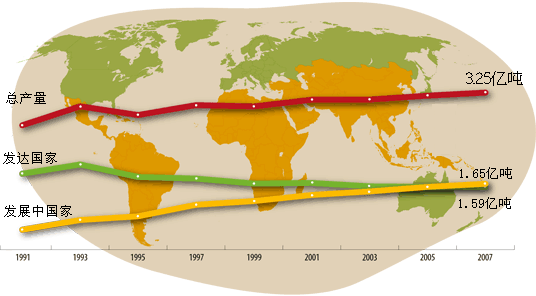
[近年来土豆在全球的种植面积趋势。红线代表总量,绿线代表发达国家,黄线代表发展中国家。]

[这是秘鲁人在烧烤刚刚收获的土豆。直到今天,土豆在第三世界国家仍是至关重要的主粮。]


[背着孩子播种土豆的彝族妇女。目前我国土豆的年产量虽然落在玉米和红薯之后,但是相当一部分的玉米和红薯成为了家畜饲料,因此土豆的粮食地位其实比这两者更重要。在土壤贫瘠且缺水的山区,土豆依然是无可替代的——几年前我去云南昭通支教时,基本上每顿饭都是各种花样的土豆餐。]

[手持土豆微笑的秘鲁小孩。]
其次,块茎毕竟是活组织,设计思想是存在地下和茎叶相连,不断新陈代谢,含水量较大,刚收获的土豆含水量可达75-80%;而不是像种子那样存够了营养物质后立即脱水进入休眠期等待春天到来——小麦和水稻种子的含水量还不到15%。因此,块茎的储存和运输难度都很大,更常见的是即挖即吃。假如储藏条件太热、太干燥或者太不通风的话,要么直接烂掉,要么开始变绿发芽,而发芽的同时会大大增加土豆里龙葵素的含量,食用后可能引发中毒。如果没有现代科技介入,即便是最佳条件下,生土豆几乎也不可能存储一年以上;所以“仓里有粮,心中不慌”的情景,对于土豆是不适用的。某些不列颠和爱尔兰民间传说宣称,把土豆引入欧洲的不是该死的西班牙人,而是伟大的英国人德雷克爵士,他在1577-1580的环球旅行中,记录了他在1578年于智利海岸遭遇土豆的经历。可惜,土豆块茎在海上不可能存活两年之久,德雷克1578年看到的土豆就算带上了船,回到欧洲也早挂了。因此引入土豆大概还是西班牙人干的好事。储存问题也是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大肆夸奖一番土豆之后,所指出的唯一缺点。

[亚当·斯密,经济学的祖师级人物,他在《国富论》一卷一册十一章估算说,土豆的营养价值是同等面积土地上出产的小麦的三倍。]
也正因为储运原因,今天的粮食国际贸易中,生土豆只占极小的比例,譬如我国的土豆出口量还不足其总产量的0.5%。不过这在当今倒是有一点意外的好处:近年来随着粮食全球化进程,国际谷物价格暴涨,但是主要受本地供求控制、不怎么参与全球交易的土豆则只受到极小的波及,因此被认为是低收入国家的“粮食安全作物”。
最后,土豆的繁殖也是通过块茎来进行。这种方式比种子的需求量要大,估计起码要有20%左右的产量留作下一季播种之用。这对于缺乏土地但不缺劳力的爱尔兰人而言不是个大问题,何况块茎法也缩短了成熟时期,足以补偿这一损失。可是,块茎繁殖更大的缺陷在当时却少有人注意:它是无性繁殖的。
其实自然界中,虽然无性繁殖的起源较早,但是现存的物种中,只会无性繁殖的却是寥寥无几,绝大多数都是要么两样兼修,要么干脆专攻有性繁殖。看起来无性繁殖一定是遭遇到了某种重大问题。对这个问题,演化生物学界的主流解释之一是所谓“红色皇后假说”,认为无性生殖的群体里,所有个体的基因都很相近,改变起来也很慢,所以很容易受到病原体和寄生虫的毁灭打击,而有性生殖因为是两个个体的基因混合,由此产生的生物多样性可以保证不会被一击全灭。(有性生殖这个问题咱们刚刚在《为什么出双入对是一个脑残的好主意》这一篇里讨论过,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参看~)
野生土豆最早是在大约7000年前在安第斯山脉的的喀喀湖区被人类首先驯化的。在驯化之前,土豆原本是有性和无性两种方式共用的,因此全美洲的野生土豆(Solanum 属)可分成多达两百余个物种,而南美人驯化时也不挑挑拣拣,如今仅在安第斯山脉被人们栽培的土豆变种就多达5000余个,安第斯也由此成为全球的土豆多样性中心。

[安第斯山区丰富多彩的土豆品种。]
这样丰富的多样性原本不必太担心病虫害问题,可糟糕的是,西班牙征服者可不懂多样性保护,他们只带回了很少的土豆品种。这在生态学上被称为“建立者效应”——原本丰富的多样性却只向外输出了一丁点,瞬间变得极为贫乏。而带回欧洲之后,土豆这短暂的几百年里又几乎全是在无性繁殖中度过,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恢复多样性;之后经由欧洲人之手播撒全球的所有土豆都有这个问题。结果就是,十九世纪广泛分布于欧洲和北美的大片土豆,遗传特质几乎全都是相同的。
这一事实有两个后果:
其一,植物病毒将在植物中长年累月驻扎下去。病毒一般不太容易杀入种子,但是在块茎中呆着却很容易,熬到下一个播种季就又可以继续嚣张下去,就算运气不好留在土壤里也很容易等到明年再趁虚而入;反正每个块茎都差不多,轻车熟路了嘛。因此传统的土豆块茎里都积累了许多的植物病毒,虽然对人体无害但是很影响产量。利用现代组织栽培技术可以创造出“无病毒株”,从而大大提高产量(成本当然也会高一些),可惜当年的爱尔兰人享受不到这一点。
其二,一旦出于某种原因,一种恶性病原体入侵了土豆田,由于所有的植株都对它同样敏感,它将以极快的速度横扫相邻的所有田地,直至扩张到另一个品种才会放慢脚步——假如还有另一个品种的话。
不幸的是,在爱尔兰发生的悲剧,正是“其二”中所描述的场景。
【灾难】
“一个英国人在一间茅屋里看见了一大群面色红润的孩子,便向父亲问道:‘您用什么办法养育了这样健壮的孩子?’这位农民回答说:‘得益于耶稣,也就是马铃薯,先生。’”
照此说来,引发爱尔兰大饥荒的“晚疫病”也许就是魔鬼的化身了。
1845年的爱尔兰已经对土豆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据估计,这时土豆提供了爱尔兰80%的人类食物,也成为家畜饲料的主要来源;而绝大部分土豆都只属于S. tuberosum ssp. andigena 这一个亚种。由于只要煮熟就能食用,因此很多爱尔兰家庭只有一口锅,土豆煮熟之后,把锅子翻过来就成了桌子;许多主妇甚至干脆都不知道如何烹饪土豆之外的事物。这段单一的链条,太脆弱了。

[版画中的爱尔兰家庭图景。]
其实当时人们已经发现土豆对某些真菌病——比如卷叶病和干腐病——颇为敏感。马尔萨斯已经针对爱尔兰问题发出了警告:算数增长的粮食不可能跟得上几何增长的人口,灾难早晚会来临。可是,每年一千三百六十万吨土豆,其中一半供人食用,如此庞大的数量,又有哪一种作物能够替代?在土壤贫瘠的爱尔兰,87%的土地被地主和新教徒控制,占人口大多数的天主教农民除了土豆又能靠什么生存?
[历史小贴士:原先爱尔兰和不列颠岛都属于天主教,后来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同时也是爱尔兰领主)因为离婚问题跟罗马教廷闹翻了,遂自立门户,成立圣公会,归属到新教门下。为了控制爱尔兰岛上虔诚的天主教教徒,英国国王陆续派遣了数万名有知识有才能有资本的新教徒"管理"爱尔兰。这也是如今北爱尔兰民族矛盾的原因。]
也许这是天命。可是和所有其它悲剧一样,最后的导火索是由人亲手点燃。
“晚疫病”(Late blight, 病原体为Phytophthora infestans)是一种来自墨西哥的土豆真菌疾病,也能感染番茄等其它茄科植物,喜爱偏暖湿的环境,感染后可以彻底毁灭整株植物。这种疾病的感染率原本不是很高,最早于1843年初出现在美国东部,当时没有引起特别大的关注。1845年,一船播种用的土豆装箱驶向比利时,这次越洋旅行的目的是向欧洲引入新品种试图对抗干腐病,然而似乎正是这船土豆,反而为欧洲带来了晚疫病灾难。

[感染了晚疫病的土豆就会变成这个样子。Phytophthora infestans传统上是归于真菌界(Fungi)的,不过近年来的分类学建议将它归入一个新的界——囊泡藻界(Chromalveolata),列入卵菌纲(Oomycota)。不过农业上仍然一直是按照真菌疾病处理的……所以这里按习惯称它为“真菌”,但并不是用的现代分类学的真菌意义。]
1845年7月下旬,晚疫病在比利时闪亮登场,迅速地向西传播到爱尔兰,向东直达俄罗斯。这一次瘟疫的后果原本并不是太严重:在欧洲大陆,农民们还有其它作物可以依赖,就算是在爱尔兰,这场疾病也只是毁灭了1845年40%的土豆收成。英国当时的总理Peel为此从印度和美国购进了价值十万英镑的玉米,可惜直到1846年2月才送抵爱尔兰,而他们那时是不肯吃烤玉米棒子的,又费了很多时间在研磨成粉上,真正抵达民众手中的时间更晚。
与此同时,爱尔兰人正在加紧种植新一季土豆以弥补去年的损失。然而,他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去年腐烂的土豆被他们留在了地里。那时微生物学还在襁褓之中,没人知道这种疾病的罪魁祸首是一种真菌,更无人知晓这种真菌随土豆埋在地里半年之后已经繁殖了多少孢子,等待着新一轮的感染。其实那时已经有科学家注意到硫酸铜对于真菌疾病的防治作用,但是“农药”这个观念那时还不存在,他们的发现没能得到推广。克制真菌疾病的王牌农药“波尔多液”(硫酸铜和熟石灰的混合物),要到三十年后才出场……
1846年的夏天,真正的灾难降临:当年温暖多雨的天气加上土壤中残留的大量孢子引发了晚疫病大爆发,幸存的植株不足百分之十;到了十月份,土豆的价格已经是去年此时的五倍。可这时的英国政府正处于混乱当中:托利党总理Peel认为保护主义不利于农业发展从而废除了《谷物法》规定的高额谷物关税,却引发党内意见分裂最终下台,新上任的辉格党Russell政府则不但施政无能,还信奉政府不干预市场。许多不列颠人觉得土豆加剧了爱尔兰人的懒惰和低贱(马尔萨斯说,“只要马铃薯体系还能够使他们的人口这般增长,远远超过了对于劳动力的正常需求,下等爱尔兰人的这种懒惰、喧闹的习性就永远不会改正”),对他们的境遇漠不关心;而爱尔兰地主则若无其事地趁着低关税把大批的谷物照常向不列颠出口。因此这场真正的灾难相对而言反倒被英国政府和民众忽视了。虽然后来政府也采取了一定的救济行动,但是来得太晚了,也太少了。
于是我们看到了本文开篇时的场景。那些场景的记录者James Mahoney说,这样的情境之下,“生者对死者的一切同情都变得不可能了。”

[立在都柏林街头的雕塑,以纪念爱尔兰大饥荒。]
可能由于气候的原因,1847年的土豆还稍微有一点收成,但是接下来的两年又是近乎颗粒无收;随着饥荒的蔓延,人体抵抗力和卫生措施都受到严重冲击,痢疾、霍乱和斑疹伤寒也开始肆虐。等到1851年灾难终告结束时,原先的S. tuberosum ssp. andigena 这个土豆亚种在欧洲基本上算是消失了,而爱尔兰的八百万人口则有一百一十万以上死去,还有接近两百万人被迫离开祖国,其中相当一部分抵达了北美。这批人永远地改变了美国的人口组成,也以最残酷的方式推动了美国的工业化进程——还记得吗?“美国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直到今天,爱尔兰的人口和土豆产量也没有回到灾难前的水平。
他们因此怨恨土豆吗?也许我们身处那个文化之外,永远不能完全理解。我们只知道,在爱尔兰最伟大的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中,土豆是一个护身符,既象征着英雄般的民族延续,又暗喻着衰败和毁灭。也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爱尔兰的人均土豆消费量今天仍然是欧洲第一(143千克/年)。灾难的历史依然是历史,无法忘却,也无法跳脱。
【后话】
是什么导致了这场触目惊心的灾难?这个问题已经被无数人问起,而和历史上所有的灾难一样,也有无数的答案被提出。有人控诉英国政府蓄意屠杀种族灭绝,有人指责放任主义经济政策的愚蠢,有人认为是人类对自然的过度改造导致天谴,有人看做是人口无限增长的必然结局。也许这样的问题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完整的答案,而这篇小短文的篇幅也不允许深入探讨每一个历史细节。因此,请允许我管中窥豹一次,只从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知识的作用。
其实,如果允许我带着现代的知识穿越回去的话,我有无数次机会可以避免这一切的发生。如果西班牙征服者知道多样性的意义;如果美国的海关人员懂得植物检疫;如果爱尔兰农民知道这是一种真菌病,靠土壤中的孢子传播;如果波尔多液提前走出法国的实验室进入田间……每一个环节,也许只需一句话,就胜过无数的政策拉锯战,拯救无数生命,也省却无数后世史家翻来覆去猜测当局是何居心——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定的“居心”,只不过是没人知道应该怎么办而已。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当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发生在今天时,政客们在抓紧机会摆姿态,科学家们却在首先关心具体的数据。
但无论如何,哪怕经历了这样的悲剧,土豆的故事非但没有结束,反而愈发在欧洲站稳了脚跟。从米勒的《种土豆者》到梵高的《吃土豆的人》,土豆逐渐成为了贫穷、朴实而勤劳的农民的象征,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土地中寻找生活。在现代的农药、多样性控制和基因工程的作用下,病害已经不再是致命的威胁;而即便是很多地方条件改善之后种上了更高产的作物,土豆仍然藏在幕后,随时准备着在动荡时期站出来挽救百姓。譬如1992年的俄罗斯,混乱的经济大重组伴随着严酷的气候,此情此景之下聪明的俄罗斯人很快就把土豆种遍了每一寸空地,甚至种到了莫斯科城外的奥斯特洛夫国家森林公园里面!

[梵高油画《吃土豆的人》,作于1885年。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我想清楚地说明那些人如何在灯光下吃土豆,用放进盘子中的手耕种土地……老老实实地挣得他们的食物。我要告诉人们一个与文明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一点也不期望任何人一下子就会喜欢它或称赞它。”]
除了农田之外,土豆在其它领域也时常进入人们的视野。就在松鼠会的博客上,就有土豆电池、不能相信的普兹泰转基因土豆实验、土豆为什么要炖牛肉、土豆是不是高热量、薯条一年会不会坏,等等等等……看来松鼠们也是土豆的爱好者。
可是,哪怕有这么久的历史、这么多的研究,我觉得土豆依然是一个谜。一种本来是用于抗饥荒的作物,反而直接导致了欧洲近代史上影响最深远的饥荒;一种便宜又营养丰富的作物,富含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矿物质,却摇身一变化作薯条薯片,成了既昂贵又不健康的全球化工业食品的样板;一种曾经因为缺乏多样性而引发灾难的作物,如今却以原产地极端丰富的多样性不断为研究者带来惊喜;一种曾经最单一最不生态的作物,如今却以新式生态轮作的方式重新进入农学家的核心视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依然是太少太少;但是正因此,这个世界才能不断地给我们带来惊奇。
主要参考文献&扩展阅读:
剑桥出版的的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Food中针对土豆的论述非常全面,是本文最重要的参考。
Peter Gray的 The Irish Famine 是爱尔兰大饥荒历史的重要著作。
Michael Pollan所著的The Botany of Desire则对土豆的文化意义给出了十分精彩的论述。这本书的中文译名为“植物的欲望”,其实原题目的意思是“欲望的植物学”,讨论的更多的是人类的欲望。
国际马铃薯年的网站 很好地介绍了土豆的现状,并配有大量精彩的图片,本文所用图片相当一部分来自此网站。
经济观察网的“土豆改变世界”专题()讲述了土豆相关的许多八卦,值得一看~
你知道爱尔兰大饥荒在有的学校是一门专题课么?看看这里: 。其中第七单元收集了和爱尔兰大饥荒有关的诗歌,很感人。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